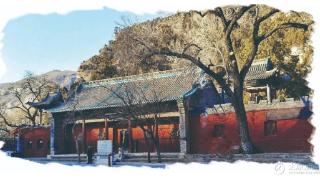- 我的订阅
- 人文
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大暴发的时代,每天都能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新闻资讯!
虽然有大数据推荐,但面对海量数据,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您通常无法真正有效地获取您感兴趣的资讯!
头条新闻资讯订阅,旨在帮助您收集感兴趣的资讯内容,并且在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可以有效节约您获取资讯的时间,避免错过一些关键信息。
高澍然:论学当以去名利
本文转自:闽北日报
高澍然(1774-1841年),字时野,号甘谷,晚号雨农,福建光泽人。他的父亲高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人,曾任福鼎县训导,十分重视以汉学训育当地士人。澍然自幼受家教影响,好学进取。他读儒家经籍,时常拿着《说文》之类的书籍,进行对照分析,以扩大它的内涵,寻求新义。并且,他常联系自己的身心实际,身体力行,因此名利心逐日淡薄,而学问却逐日进步。
嘉庆六年(1801年),高澍然选为拔贡,同年乡试又录取为举人。嘉庆十年(1805年),礼部会试后,任职内阁中书,半年后调任侍读。但因他认为“治身心自远名利始”,从小淡泊名利,以为官场酬酢,不利于做学问。又因父卒,自恨在外为官不能尽孝,便决意辞官回家,专心致力于儒家经籍和古文的研究。在老家定居时,他从不以个人私事去麻烦县令或郡守等地方官,但有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常勇于陈述自己的意见,力争为百姓多办好事。如修文庙、建义仓、筑县城等事,他都能率先为倡,深得当地百姓的信赖。
道光九年(1829年),他应聘到省城纂修《福建通志》,与陈池养、张际亮等17人为分纂。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福建通志》总纂陈寿祺病故,当年5月他接任《福建通志》总纂。这时《福建通志》已大部编纂就绪,准备脱稿付印。由于省里有个当权者与陈寿祺有意见,就唆使数人发难,指摘《福建通志》稿有“儒林混入、孝义滥收、艺文无志、道学无传、山川太繁”五大缺点,并要求将原稿分散审核。
高澍然感到非常气愤,立即上书郑方伯和王观察,对这位当权者所提志稿的五大缺点,根据通志体例和历史事实,据理力辩,一一给予驳斥。他认为,当时太史陈恭甫事迹没有入志,并非主笔有私嫌,而是资料未收集齐全,岂能因此而否定他人说是“儒林混入”?至于“孝义滥收”问题,他认为采访册是依据事实录用,不尚空谈,决非滥收。所谓“艺文无志”,他认为“经籍”已有志,“艺文”则不必有志。因为福建自唐朝至今,作者辈出,经籍书目繁多,如果艺文人志,就要增加诗文数百卷,这成什么体例呢?再说奏议、论说、政要等在序记和各门类及本传未尝少略。至于“道学无传”问题,他认为道学名传创于元朝,标目用“道学”就不确切,钦定明史中就已不用了。对于那些有突出历史功绩的道学家,已在“儒林”“文苑”编目中特别立了传,岂能说“道学无传”吗?最后关于“山川太繁”问题,他认为山川志,每本不过30余篇,合起来不足10本,图经地理应该详细,山川当然不能少略。以上所谓志稿不善五事均系故意作难,无事生非。
高澍然论通志体例,明白简要,句句在理,足以扫云雾而见青天。忠于史实,坚持原则,敢于触犯衮衮诸公,明知不敌而敢于斗争,是个道地的史学家。同时他坚决要求,在没有缮写好副本以前,不能将志稿分发给他们去无理勘校,以免费时六年资费数万金、辛辛苦苦编成的志稿毁于一旦。但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题释忿,致使糜费四万金,备群力6年之久的《福建通志》没有付印出版。由于个人只身在省,高澍然不愿与他们多费唇舌,坚决辞去通志总纂之职,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回到光泽。在光泽,因县志80年未修,其体例也不完整,县令胡国荣和觉罗永安先后聘请他纂修《光泽县志》,但因“经费未集,采访有待”,修志工作曾一度暂停。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修成《重纂光泽县志》30卷,很有独到的见解,受到地方人士好评。
高澍然品行高洁,文才过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应聘到厦门玉屏书院主讲。在他的精辟讲解和分析下,为时仅3个月,厦门之士对古文学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各地慕名云集而来受课的人,多得连校舍都无法容纳。到了回光泽的那一天,诸生远送,人人泪下。
高澍然竭毕生精力为地方志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也曾在光泽杭川、邵武樵川两书院亲督教学,真可谓桃李遍地,花开四季。在此期间,他列举朱子学规,细心引导学生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他力求讲学其间,不以为劳。他论学以去名利心为第一要义,教学上他注意启发,能根据学员学科目“勉以自得之道”。
高澍然为人正直,他一生除读书研究学问外,另无其他嗜好,即使是书画古物,也未留意过。他胸怀淡泊,不为名利所动。嘉庆十年(1805年)礼部考试以后,某相国曾复阅他的试卷,暗自赞赏,有意罗致自己门下,表示愿意引见,以建立私人关系。但高澍然认为以文字自托门籍非君子行为而拒绝了。他曾对人说:“座主考官一日文字之知,而自托门籍,曰师曰受业,岂守道君子之所为邪!”澍然在京师为官时,某大臣得知他已丧妇,欲以女嫁给他为妻,他不愿以此攀附权贵,而婉言谢绝。嘉庆十五年(1810年),汪志伊来福建任总督,府学教授吴贤湘将澍然所作文章推荐给汪。汪对高澍然的文章十分赞赏,要求高澍然作《道一论》一文。高澍然说:“我非应试生,奈何以此试我?”加以拒绝。后来汪志伊的儿子以所修的古文请求他指正时,他则直言不讳,一一加以讲评。
高澍然对唐代韩昌黎的文章,非常爱好,细心研读达30年之久,精通韩的文旨和写作要领。他经过慎重考证,依据韩文的原文原义及其遣词论事的雄伟气魄,详加注释和评述,辑成《韩文故》一书,成为当时研究古文学的一大宗师。
高澍然是个有成就的史学家。其著作有《诗音》15卷、《春秋释经》12卷、《易述》13卷、《诗考异》30卷、《学习之文牍》10卷、《论语私记》2卷、《福建历朝官绩录》40卷、《闽水纲目》12卷(附图一卷)、《河防》三编各1卷、《抑快轩文集》73卷、《韩文故》13卷、《李习之文读》10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病故于家中,享年68岁,县人奉祀他于乡贤祠。(黄睦平 整理)
以上内容为资讯信息快照,由td.fyun.cc爬虫进行采集并收录,本站未对信息做任何修改,信息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快照生成时间:2024-03-25 05:45:01
本站信息快照查询为非营利公共服务,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信息原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