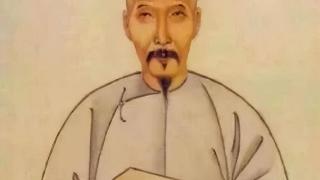- 我的订阅
- 人文
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大暴发的时代,每天都能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新闻资讯!
虽然有大数据推荐,但面对海量数据,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您通常无法真正有效地获取您感兴趣的资讯!
头条新闻资讯订阅,旨在帮助您收集感兴趣的资讯内容,并且在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可以有效节约您获取资讯的时间,避免错过一些关键信息。
《阅微草堂笔记》手稿寻踪
本文转自:沧州日报

沧州博物馆纪晓岚塑像

《容安馆札记》相关记载内页

《闲处光阴》相关记载内页
本报记者 魏焕光
今年是纪晓岚诞辰300周年。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文言笔记体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尤为著名。但这部书的手稿下落一直成谜,不但学界不知,就连纪氏家族后人也不知其去向,堪称憾事。
日前,一篇名为《手稿去哪儿了?》的文章引发关注。作者吴树强经过考证,在文中提出了手稿下落新的重要线索,让我们共同探究。
《容安馆札记》指出查寻路径
《闲处光阴》详记手稿沉浮
吴树强是沧州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也是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的铁杆粉丝。1月8日,他在阅读微信公众号“锺书掠影”推送的《剑、雷、虹皆有雌雄之别》一文时,发现钱钟书先生《容安馆札记》之二十一则中,对《阅微草堂笔记》一书有很多评论和记述。尤其是下面这段文字引发他极大关注:
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修洁而能闲雅。《聊斋》较之,遂成小家子。乃郎汝佶轻家鸡而逐野鹜,苦学《聊斋》,何耶?参观卷二十四,可谓“日进前而不御”者矣。
这段文字中,钱钟书先生将《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进行了简单比较,并作出评价。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段话后,钱先生又用小字补充了“笔记稿本下落见《闲处光阴》卷下”一句。很显然,钱先生认为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才补充上去。而正是这13个字,引发了吴树强强烈的兴趣。热爱地方文史的他,立即通过检索找到了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闲处光阴》,该书刊印于民国四年(1915年),作者署名为“抟沙拙老”。
相关记载到底在这部书的第几则?钱先生并未说明。吴树强通读卷下部分,终于找到了下面这段翔实记载:
纪文达公笔记(《滦阳消夏录》《续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稿本藏公孙香林观察处。余客宜昌,观察为宜昌太守。余以世谊,交复不浅,乞借一阅,必言之再方允。观察之于手泽,可谓能守者矣。讵意下世不数载,凡所藏物,尽行散失。丙申(1896年)秋,余在京见此函陈于琉璃厂书肆中,缘缮录既不工整,又加以涂抹纵横,故久不售。忆昔之贵愈拱璧,不觉为之黯然,询其直,曰京蚨二千余,辄如其索购之。稿乃公手自校,可宝爱也。丙午(1906年)夏,济东观察徐公驻临清催运,余为随员,观察幕客某君闻余携是书,向余索借,久久还来,见旧讹误处,间以硃笔正之,不胜愤懑。既而自咎曰:余过矣!唐杜暹藏书跋尾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谅哉!谅哉!
纪晓岚谥号“文达”。纪晓岚次子纪汝传的长子名为纪树馨,曾任职江西宜昌,香林是纪树馨的字。“公孙”意为文达公之孙。纪树馨是纪晓岚十分疼爱的一个孙子,纪晓岚去世后,《纪文达公遗集》就是纪树馨整理的。纪树馨对祖父的手稿可谓珍爱有加,以至于有着世交情谊的作者抟沙拙老,提了两次要求才得以借阅。令抟沙拙老万万没想到的是,纪树馨去世后,其“所藏物,尽行散失”。更令抟沙拙老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竟在北京琉璃厂一个书店内,看到了当年曾借阅的手稿并以“京蚨二千余”的一口价买了下来。“京蚨二千余”折合人民币多少钱不得而知,但此定价想必不菲。后来,抟沙拙老把此手稿借给一位幕僚阅览。谁知这位幕僚太不讲究了,擅自用笔纠正自认稿中讹误之处。抟沙拙老悔不当初,但碍于情面,只能引用唐朝宰相杜暹诫子的话来自责和抒发愤懑。
追踪到此,弄清这位抟沙拙老的身份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是找到手稿下落的关键。经过检索古籍目录,吴树强获取了新的线索,原来抟沙拙老的本名为彭邦鼎,同治《恩施县志》卷九《流寓》里记有他的生平:彭邦鼎,字配堂,江西南昌人,工书善词赋,晓昆山音律,嘉庆间为佟郡伯幕宾,赘樊副将家,后官山东巡检。
面对这个查询结果,吴树强在文中写道:“由此可知,至少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天,甚至直到此书出版的民国四年(1915年),《阅微草堂笔记》的手稿都很可能一直珍藏在这位抟沙拙老的家里。至于后来流落何处,暂时不得而知,欢迎读者师友不吝指教。”
贺葆真曾追问手稿下落
“郑本”序言提及相关信息
为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记者随即又采访了沧州纪晓岚研究会会长李兴昌。
李兴昌说,《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作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全书分为《滦阳消夏录》《槐西杂志》《如是我闻》《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集,近40万字,共收故事1200多则。该书记述的主要是神鬼狐怪故事和社会见闻,都是篇幅短小的随笔杂记。但是,这部书的手稿今天不知身在何处。纪氏家族2021年重修家谱的时候,族人也曾试图寻找手稿下落,但当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李兴昌说,他已关注到吴树强的文章,同时又向记者提供了另外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来自纪氏后人重修的家谱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一天,河北武强人贺葆真向纪晓岚裔孙纪堪谨询问纪晓岚手稿的去向。纪堪谨称纪晓岚部分手稿被梁上君子焚毁。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的儿子,和纪晓岚的后世孙纪钜维颇有渊源,有《贺葆真日记》传世。这段问答中提到的手稿具体指的什么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外一条线索则来自清人郑开僖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序言。李兴昌说,《阅微草堂笔记》有两个版本最为著名,一个是嘉庆五年(1800年)纪晓岚还在世时,他的学生盛时彦的刊印本,世称“盛本”;一个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郑开僖刊印本,世称“郑本”。郑开僖在书前序言中记叙了这次出书的缘由。原来,上文提到的纪树馨的弟弟纪树馥当时“来宦岭南,从索是书者众”,便“因重浸板”,再次刊印《阅微草堂笔记》。郑开僖为此称赞纪树馥“谨有学识,能其官,不堕其家风”。这里提到的“是书”,是纪晓岚的手稿还是嘉庆五年印刷的“盛本”,从文字上看不出来。
期待各界提供有价值线索
推动纪晓岚文化研究走深
文人手稿体现着作者的创作过程,是有生命印迹的特殊文献,让后人睹物思人、满怀敬意,同时兼具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尽管以上线索还需要文化收藏、古籍研究等领域的有关专家进一步综合研判,但寻找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手稿的步伐,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吴树强和李兴昌均表示,今年是纪晓岚诞辰300周年,他们希望社会各界能提供相关线索。相信随着更多线索的出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手稿的具体下落会更加明晰。而这项发现必将对沧州乃至我国纪晓岚文化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一旦手稿重新面世,它必将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丰满的、留存着生命温度的“一代文宗”,必将为乡土文化注入更加渊深厚重的内涵。
以上内容为资讯信息快照,由td.fyun.cc爬虫进行采集并收录,本站未对信息做任何修改,信息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快照生成时间:2024-01-18 11:45:02
本站信息快照查询为非营利公共服务,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信息原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