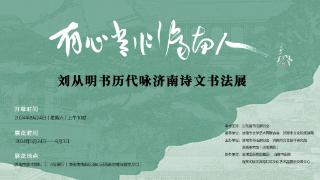- 我的订阅
- 人文
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大暴发的时代,每天都能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新闻资讯!
虽然有大数据推荐,但面对海量数据,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您通常无法真正有效地获取您感兴趣的资讯!
头条新闻资讯订阅,旨在帮助您收集感兴趣的资讯内容,并且在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可以有效节约您获取资讯的时间,避免错过一些关键信息。
陈加林著名书法家——名家辑评

1962年出生于安顺,笔名林零、子牛。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人大政协书画院副院长,贵州孔学堂书画研究院副院长,贵州文史馆特约研究员,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贵阳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画院学术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委员。
书法:多次担任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国展评委,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全国书法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及碑林勒石。作品数次入展全国书法展及专业创作展。入选『三名工程』展,获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届、第六届书法创作一等奖。多部作品被国际国内友人收藏,出版有数种《作品集》专著。中国画:作品《黔山秋映》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民族双年展;2016年作品《泉眼无声》特邀参展第二届民族双年展;《古城之韵》入选大道有痕2018中国名家金陵画展;《大山之韵》入选『新时代新气象』2019首届全国山水画双年展。
第七届兰亭奖评委陈加林作品

名家辑评
云霞明灭或可睹——陈加林书法艺术臆说
冯剑星
古来作书之人,有小才情者,亦有大才情者。夫小才情者,以循规蹈矩为能事,信而好古,食而不化,拘泥于章句之间,雕琢于腐朽之内,穷以白发,豁以马齿,兀兀不舍,或有小成,此之作者,终其一生,总不见大道之所在;然大才情者,得天赋之所予,弃燕雀之小志,追晋唐之风雅,游弋于古贤之侧,见诸于性情之中,坐云读雨,驱古入今,不以古为古者,亦能今为今矣,万象在胸,风骨潇洒于笔墨之外,可见自我之所在。余知陈加林先生也久,读其书作也多,披览之间,嗟叹再三,深以为加林先生之书作,当跻身古来大才情者之间而无愧色。

余观加林先生之书作,能在庙堂之高,亦能在江湖之远。能入张旭怀素之堂奥,亦能在简牍书帛之民间,合乎古今之变化者,方是不古不今之高手,亦是亦我亦古之独特风格。其草书取秦汉简牍之质朴,亦取章草之古澹浑厚,取晋唐名家之意韵自然,亦取明清学人之体式气度。以方写圆,以圆作方,高标尘外,独窥古今。清人朱履贞《书学捷要》云:“书之精能,谓之遒媚,盖不方则不道,不圆则不媚也。

书贵峭劲,峭劲者书之风神骨格也。书贵圆活,圆活者,书之态度流丽也”,能解此语之者,方可见加林先生出古入今之手段,思接千载之遗想。若以古鉴今之流辨而思之,加林先生能师古人而求门径,师造化而求自然,师心源而求自我。师古人可知法之所在,师造化可知道之所在,师心源可知我之所在。加林先生之书作,是能向技求道而得自我之深心者也。“穷神知化,探玄钩沉”之理,诚不欺人也。
夫草书之变,古草张索者为一变,今草旭素者为一变,宋之黄山谷者为一变,至于王铎、傅山者为一大变,至于民国以来,当又是一变也。其所变者,在于体式也,其所不变者,在于法度也。然变之难者,在能我,能今,能新,若不如此,不可谓之变矣。陈加林先生之草书所变者,在笔墨,在性情,在结体,在气韵。其于笔墨所见着流美为其韵,古拙为其质,二者相融相生,自见“长鲸喷浪,大鹏搏风”之气象。

笔之所作,心之所造。妙绝毫末之巅,象出物理之外;其性情所写者,当能心手双畅,写心畅怀之所在。挥毫落墨,意象无穷,天机清旷,烟霞即生;在结体者,其能融隶篆入草,中锋侧用,侧锋转换,绞锋沉穆,愈奇愈古,愈古愈今,清光照人,惊电飞霜,是张旭之笔法,王铎之气势,傅山之纵逸,山谷之跌宕;其气韵者,在能以生写熟,以古写今。在正奇变化之间恣肆挥洒,吸风饮露,嘘气成云,情之所至,锋发韵流,信手之涂抹,草草不及处时出古人之右。如此,才见加林先生大才情处,襟怀之所寄,心源之所生。

师古之法在能得其心,出今之法在能出我意。不以古为古者,见我之所在;能以我为古者,方知今之所在。陈加林先生之书作,所以能新者,在其取法之博,入古之深,造我之力。观其书作,不以一家一户之而立足,近法二王行草之秀逸,远取汉砖秦瓦之驳杂,石刻造像之厚重,明清诸家之典雅,相互融合,奇正而一,为血为肉,为骨为气,出于高华而去其粗野,得其奇逸而化其浅陋。风神一变,淋漓尽致。读来使人叹赏加林先生创造之力,变化之趣,自我之意。以散笔入草,大开大合,从容自然,妙臻于古,法见于今,大可见加林先生腕底风云之气,纸上江山之胜。
久闻黔中山水至佳,非能以图画所能尽知也,惜未能一游为快耳。今读陈加林先生之书作,溪山行旅之清秀,苍烟暮雪之真容,使人有尘外之想,卧游而大可尽揽也。太白所谓“云霞明灭或可睹”之语,不亦此之谓乎?

半含春雨半垂丝——陈加林书法艺术散论
文|龚勤舟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门类里,有两种文化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和东方人群的独有思维,它们就是诗词和书法。在此强调这两种文化并非是在降低其他优秀文化的品位和价值。就汉字本身而言,诗词和书法这两个文化门类将人类最伟大的语言文字表达得最为直观,也最具深义。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在生命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和书写,因此,语言和文字这两种最基础的文化方式承载着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
也许,正是这两种最基础的文化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无穷的魅力和蓬勃的生机。凝练而又透辟的语言养育了最伟大的文学家,保存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优美而有意趣的文字成就了可以进行无限阅读和欣赏的书法艺术。文字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记载,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存在的守望者。

既然文化是人类流衍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作为早熟的诗词和书法,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传统文人。长期以来,在文字的视阈里,研习书法已经成为文人们传达人生理想、寄托内心情感的一种文化方式。他们遨游在书法的海洋里,或是倾诉、或是欢笑、或是垂泪、或是高歌。
总之,书法带给他们无限的力量,他们已经将这外在的表达方式内化于自己的心灵了。早在一千六百年前的东晋时期,书法于汉字的大变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于是,赋诗论书、畅叙幽情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情趣。

王羲之家族生逢盛世,受玄学浸染,潜心于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将书法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并使之成为时代的文化核心,因此,二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确立了典范意义。二王书法对后世的影响似乎从未断绝,历代的皇亲贵族、文人骚客都将其书奉为圭臬,当代的大部分研书者也将其看作无与伦比的法宝,感同身受,顶礼膜拜,陈加林先生便是其中的俊杰。
加林先生浸淫二王多年,他悉心体会着其行草书法的精华。二王书法有着臻于完善的笔法,抽刀断水,兔起鹘落;有着丰富精到的点画,玲珑出俏,穷极变幻;有着外柔内刚的形体,虚灵挺拔,温润儒雅。二王书法将精能和率意、秀妍和雄健进行了完美的协调,流溢出静穆简淡、秀逸雅致的光芒。

但是,在传世的二王法帖中,几乎所有的法帖都是唐人临摹或单刻、丛刻而成,这让研书者不能尽观其书的笔触,加剧了研习的难度。与规范的法帖相比,二王的尺牍包容了更为广阔的意蕴,那些残破的尺牍,吉光片羽,寥寥几行却可以让人玩味无穷。灵动而又果敢的笔锋时藏时露,顾盼自然的点画传达了生命的活力。
平心而论,尺牍诚不及法帖在结字上的严谨,但那随心所欲的宽松心态,你来我往的起笔收锋,造就了二王书法特有的笔势和法度。在其尺牍中,《丧乱帖》、《初月帖》、《频有哀祸帖》、《中秋帖》等对后世的影响甚为深远。《丧乱帖》以情感的随机波动取胜,笔法的粗重和空灵丰富了作品的内蕴;《初月帖》保存了汉隶、章草的笔意,作品留有古朴厚实的遗踪;《频有哀祸帖》加入了适当的牵丝引带,不激不厉,有的放矢;《中秋帖》则以“一笔书”来完成作品,它将连笔发挥到了极致。

先生追踪二王却又不囿于二王,作品中常常透露出取法唐宋的底蕴,他对文字的造型用心良苦,在尊重草法之时,努力进行着长短曲直、斜正疏密的恰当安排,在不变中应万变,在变化中驾轻就熟、举重若轻,颇有几分米芾的“四面锋”。他喜欢写唐诗以抒己怀,唐诗的空灵和丰腴或许更适合于其书法的气质和风格,在尺牍《韩愈诗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浑厚奔腾的笔墨展示着风樯阵马的雄壮,逸尘断鞅的笔性,干裂饱和的墨韵,翻滚抹扫的率意,让作品顿显波澜老成之态,大有“纸穷墨渐燥,蛇蚖争入卷”(陆游诗句)的霸悍风采。

然而取法二王的研书者,大多注重技法的锤炼,所以作品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人工雕琢的痕迹。加林先生长期私淑二王书法,作品同样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其草书尺牍点画和引带奇异多变,字法和章法多有考究,展示出颇为深厚的功底和才华横溢的灵气。但是,那些精妙的安排让作品生发出雕饰的气息,冲淡了个人性情的自然发挥,作品尚未达到心闲手敏的层次。
加林先生的行草,不但尽显帖学之意,而且能够将碑意引入行草,既生奇形,又非鬼怪,既得浑朴,又弃粗陋,较好地把握了碑的力度和分寸,溶盐于水,点石成金。

草书作为最简洁的书法形式,它将汉字的造型尽可能地融化在笔和墨之间。笔墨挥就而成的作品记载了书法家的艺术心迹和生命写照,酣畅淋漓的线条在瞬间铺展开来,它们的奇特和多变让整个作品显得丰富而又烂漫,空灵、清雅、散淡、哀怨等人类可能具有的情愫,随着笔的力量出没于枯湿浓淡的墨痕里。
草书既让人的心境在最直观的造型艺术中流淌开来,又让人之为人的最为鲜活的情感在笔墨游走的瞬间定格。草书作为快和慢的交融,其“快”,既是日常时间的迅捷表现,又是心性的痛快倾泻;其“慢”,既是内心世界的层漫溢,又是情真意切的默默传递。

如果说笔的疾驰徐缓、墨的虚实枯润表现出书法作为艺术品性的完美,那么经历千百年历史动荡而流传至今的草书杰作便是人类跨越时空的永久诉说。笔墨作为情感的寄托,折射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蓄积着人类的无穷智慧,那些电闪雷鸣的书写和含情脉脉的意会,让草书从二元对立的两极演绎成海纳百川般的交融。
常言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社会的变迁致使草书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和自我丰富。一千多年来,草书的外在形式从高不盈尺的信札、手卷延展为明镜高堂里的鸿篇巨制,从手心把玩的小品发展到驻足观摩的大作。它的内在技法从运指灵便、八面出锋的丰富字法演变为运腕使臂、曲行环转、气势纵横的整体章法,这种尺寸和形式的改变,折射出艺术笔墨的时代之新。

晋唐以后,明清成为草书艺术的又一座巅峰,明清时期的草书英杰们从形式和情态的层面赋予了草书的生机,祝枝山、陈白沙、徐文乐、倪元璐、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傅山等书家对草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草书意态将书法含蓄的韵味和严整的法掩藏起来,进而竭力表露着张扬的个性和瞬时的激情。
其浓重的线条有着夺人眼目的视觉冲击力,新奇的字法有着鲜活的时代感。如若我们将以上书家的草书细而论之,又会发现他们的草书取向和书写技巧有着一定的差异。祝枝山、陈白沙和徐文长格外强调书写的一次性,狂风暴雨般的淋漓恣肆在他们的草书中表现得最为浓烈。但是这种迅猛的发力既展示出书家人的才情,又流溢出书写的草率和字法的荒疏。

铎的草书在抒写性情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以参差引带、胀墨浑重取胜,将二王书法进行了夸张和放大,他的草书字法严谨,极其重视字与字之间的承接关系。王铎似乎在着意追求结字的完美,他在圆转与方折、顿挫与硬拗之间绝不忽略瞬间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其作品的一点一画都需要在规定之中完成笔法的到位处理,他宁可让作品出现补笔的痕迹,也不轻易让单个文字变得草莽粗陋。
诸如此类的书写取向,表明他坚定不移地根植于晋唐书法,但是由于明清时期书法创作形式的改变,大字草书的书写不能完全依照过往的技法,随着书写材料和发力的变化,致使字法和笔法不能臻于完美的境界。

然而,王铎的出现却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书法的历史空间,字法和笔法虽不如晋唐宋元时期那样精致,但是由浓淡枯润的墨色对比、文字结构的非常规处理、笔迹连绵的空间取势等一系列元素形成的前所未有的书风却如同潮水般席卷着中国书法史,以至在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受用无穷。
如果说王铎是在悲剧性地尽全身之力捍卫晋唐时代书法的精妙字法和笔法,那么近代以来的书家则是在有意识地瓦解字法的完整性。晚清以后,随着碑学的兴起,一代代书家在赵董书风盛行的大背景下将注意力转移到对碑籀钟鼎的研习上。碑学的发展为振兴阁帖之衰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于是融碑入贴、碑帖熔铸的美学取向成为时代的主流。


赵之谦、于右任、李叔同、谢无量等书家在碑帖共融方面贯注了毕生的心血,使其成为开宗立派的书法英杰。然而,碑帖共融作为一个开放的课题,其中混杂着无限的对立和交锋,稍有不慎,便会出现邯郸学步的惨状。陈加林先生在临习二王法帖时,极其重视对北碑墓志的取舍,他的草书,在凝重的碑版和飘逸的阁帖间进行着精心调制,其草书起笔收锋暗含碑意,章法活脱凸显生机,线条厚实又不失灵动,气韵贯通更为豪迈,这一系列因素汇聚于他的草书,溶盐入水,丝毫不见生硬和焦躁的陋痕。

以我之见,先生视指法和腕臂为研书之两翼,以内在性情来调节两翼的平衡,所以他的大字雄健小字精当,谋篇布局寓雷霆万钧之势,细节经营有春蚕吐丝之妙。近年来,他钻研大草,借助扎实的行书功底,深入揣摩草书文字的造型,认真炼造草书飞动厚重的线条和新奇开阖的章法。他对草书的理会和书写,经过千锤百炼,已经内化于心、外发于手,因而展示出高迈的艺术水准,在当今书坛少有与其并肩的草书俊杰。他通过研究中国书法史,尤其是草书在书法史上的传承谱系,全方位地体悟着传统和创新的内在规律,在草书书写的矛盾对立中捕捉着和谐统一的元素,在不同的篇幅形式中解决了因字法、章法引起的症结,他从传统出发,同时又在打破传统草书固有的造型,其作品让人意会到书写的合理性和新鲜感。

较之其他书体,草书强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准则,法度固然重要,但当法度日趋完善时,需呈现出无法之法。“心忘于手,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王僧虔语),正是心手两忘造就了不定法,渲染出“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观之末,某来无止”(《庄子•则阳》)的气象,让草书臻至书法的最高境界。

陈先生的草书着意于烂漫、真淳的表达,因笔成形,着墨生趣,心手自如;故而草书自然。他在心和手之间领会着™始由笔墨成,渐次忘笔墨,心手两相忘,融化同造物”(吴镇诗句)的深义,其八尺条幅《张九龄诗望月怀远》便是一例。作品通篇散逸着“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聚散有度、大开大阖的章法令人震惊,牵丝引带的线条增加了笔墨运动的节奏和幅度,显示着文字的奇崛和桀骜。此件作品,他在章法的摆布上受到明清书风、尤其是王铎草书的启发。王铎的草书强调高质量的线变,力求在线的旋转盘缠中显示草书的夺人之势,让草书圆转的用笔展现出帖学笔法的精纯。王铎草书的盘缠引带,往往是从上一个字的收笔处起笔,从内涵上说,诸如此类的引带并不能靠线条来贯穿草书笔势,它只能沦为谋篇布局的一次装饰,沦为空间对比中的视觉效应。

加林先生在学习王铎时,在体会草书的盘缠和由胀墨引发的文字构成时,关注着其草书邻近文字的奇异连结,由此生发出章法的新奇和字法的险绝。表面上看,其文字的支离取势类似于王铎,但又有深层次的差别。他的草书虽有主观安排之嫌,但支离有余,摈弃了做作之态。他并不完全笼罩在流畅快捷的帖意里,而是揉入了大量的北碑笔调,中锋和侧锋双管齐下,方折和圆转并驾齐驱,线条在自然流走的同时生发出坚刚、生涩的起伏跌宕,正是北碑的兼容,丰富了作品的提按顿挫。由此可见,他在汲取二王精髓、浸入王铎形式时,融会了个人对草书独有的思考。

在中国书法史里,酒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五谷的精华,酒在中国文化里流溢出挥之不去的效用,它以水为形,以火为性,兼顾着阴柔和刚强的性格,吐露着甘美和苦涩的气息。酒是一种养料,它滋润着人类的心灵;酒是一种品性,它助长了生命的激情;酒是一种力量,它赋予了艺术的真谛。
古往今来的草书名家,大多恣情于酒、留恋于酒、倾心于酒、迷醉于酒,作为写意之尤的草书,又最为直接地表达着“书为心画”的意念。气贯山河的胸怀,奔逸天岸的豪纵,鸿飞兽骇的身姿,临危据槁的形态,声断南浦的节律,诸多因素作用于草书,使之“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
既然酒是艺术的乳液,那么它必将熏染着、催化着书家的性情,使其创作出惊天动地的作品。李白在《赠怀素草书歌》里写到:“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顿飒,落花飞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既然酒是艺术的乳液,那么它必将熏染着、催化着书家的性情,使其创作出惊天动地的作品。李白在《赠怀素草书歌》里写到:“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顿飒,落花飞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张旭三杯草至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正是酒的到来,成就了张旭,相传他每次大醉后便要呼叫狂走,索笔挥酒,其书张狂,龙飞凤舞,恍若神助。美酒让张旭和怀素进入了书法的玄妙境界,他们拒绝了刻意的雕琢和安排,将有形的汉字升华为抽象的点线,使草书在人、纸、笔、墨的共同作用下表现出最凝练、最自然的艺术景象。如此看来,酒对于草书创作的影响主要在于它能够拓展书家的心境,滋养书家浪漫的性情。加林先生往往氤氲在淡淡酒意里进行着草书的研习和创作,所作草书多有随性传情的迹象,其《王昌龄诗芙蓉楼送辛渐》便是一例,完备的草书技法、清新雅逸的气韵伴着流畅的笔情,确是“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苏轼诗句)的写照。

所书条幅《莫放春秋佳人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同是酒后遣兴,却另有一番风味,作品假羊毫为用,在中锋的运行下,用笔尽显篆隶之法,字与字之间连笔较少,行与行之间错落有致,厚拙稳健的笔力,遒劲婉转的点画,气格豪迈,拿云攫石,瓦棺篆鼎,古意猎猎,从容儒雅,谦和凝重。作品左上角辅以小行书加以点缀,大小不一的印章分布于黑白失衡之处,释文、正文和款识三部分文字交相辉映,主次分明,颇具几缕时尚的气息。加林先生有着满腔的激情和对经典书法的深度理解。他以行草为主、篆隶为宾,在研习的过程中追寻着笔墨的法度和妙契天机的造化。
依我之见,他的书法已经具有高度的表现力,其书法艺术正步入”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阶段。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他将在险绝和平正、技法和心性的两端进行调和。虽然书法的无上之境让人难以企及,但是加林先生怀着“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壮志孜孜探求着书法的时代气象。
以上内容为资讯信息快照,由td.fyun.cc爬虫进行采集并收录,本站未对信息做任何修改,信息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快照生成时间:2024-05-19 05:45:03
本站信息快照查询为非营利公共服务,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信息原文地址: